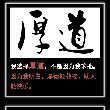中学生文萃读后感1000字
1个回答
2016-05-16 · 知道合伙人教育行家
关注
![]()

展开全部
《中学生文萃》创刊时,我上高二。正是对写作和投稿极其狂热的时候。和很多人一样,我从心底里欢呼这本杂志的诞生。我给它起的宣传语是:这是一片属于中学生的沃土,自己耕耘,自己收获。
当时,并没有公开征集杂志的宣传语。我和主编丁仁祖老师认识较早,我知道杂志创办的过程,我说,中学生写、中学生办应该作为我们的一个特点。这条宣传语后来印在杂志上,也印在宣传页上。
最早的特约中学生编辑有两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宝鸡的张福刚。当时,想叫特约中学生编委,时任陕西教育学院院长没有同意,他说成年人叫编委,中学生还是叫编辑吧。
每次去教育学院,我都会提一些刊物,是我平时收集的。我建议丁老师学习人家的长处,特别是装帧设计,希望能洋气一点。我不但当面给丁老师说,还多次写信,但是,却很难改变,一是杂志没有钱请高水平的美术编辑,二是丁老师认为实在一点好。也许这也是刊物的一个风格吧。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丁老师一个人在办这个刊物。作为学生编辑,我力所能及地帮他做一点事。我以杂志的名义约不少人写稿。一九九三年上海首届东亚运动会点燃圣火的“东亚圣女”阎华也回信了。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的童话作家马璇应约寄来了稿子。丁老师还让我以他的名义给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写信,希望他为刊物题词,后来他果然题了词。我也帮着看一些读者来信,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中学生说启功写的“中学生文萃”这几个字不好看,像火柴棍棍。他可能不知道,这正是启功的风格。
我的那些喜欢文学的好朋友,也被我介绍了过来。暑假,我们一起帮丁老师编稿,校对杂志。周盼红住在市二十六中学,他骑自行车过来,进教育学院大门时,没有人提醒他要领一个车牌,等到出门,问他要,他没有,就走不了了。后来只好把车锁到车棚,坐公共汽车回家。他曾办过一份叫《追求》的手抄报,刊首语是他写的,我选登在杂志上。刘峰的一组散文诗《被雨声围困的村庄》也是我编辑的。之前,在学校,我们有过短暂的交流。
我和很多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教育学院。王琪那时候还在陕西第一工业学校上学。张斌峰高考后,来编辑部送稿,他后来做过杂志“心灵之约”栏目的主持人。周盼红也当过一个栏目的主持人,他的笔名叫安达。一九九四年暑假,在编辑部,我们送杨广虎和阎妮一起去北戴河参加文学夏令营。
我们在教育学院的食堂吃饭,晚上就住在编辑部里。铺一张凉席在楼道,几个人躺在一起,凉风吹来,很是惬意,我们经常聊到很晚才睡。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我们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做过报纸编辑和采访工作。在《中学生文萃》的这段经历,应该算是新闻生涯的最开始吧。
上大学后,我和杂志联系越来越少。后来因为报刊整顿,杂志准备停办,我还写过回忆的文章,后来又说可以继续办下去。再后来,丁老师不再担任主编。
杂志早已更换了名字,但是,我们这些人,还是喜欢以《中学生文萃》的名义聚会。时间流逝,如同小学生放学,开始是排着整齐的队伍,人数众多,颇具规模,走着走着,各到各家,长长的队伍变短了。每当想起,难免会有一丝丝的难过,过去的日子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有的人也联系不上了,比如燕怡。我上大学后,他给我寄样刊,给我写信。我记得有一次他为杂志拉到了赞助,写信告诉我,好像自己得到了很大一笔钱,兴奋之情洋溢在纸上。而现在也找不到他了。
去年夏天,弟弟帮我整理堆放在老屋里的那些杂志,其中也有《中学生文萃》,实在太多,他留下了一些,大部分都处理掉了。我感到惋惜,但也不能责备他。回到家,再看当年的杂志,竟然感到有一点点陌生。如此投入地去爱一本杂志,可能只有少年时代才会那么去做,可惜我的少年时代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当时,并没有公开征集杂志的宣传语。我和主编丁仁祖老师认识较早,我知道杂志创办的过程,我说,中学生写、中学生办应该作为我们的一个特点。这条宣传语后来印在杂志上,也印在宣传页上。
最早的特约中学生编辑有两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宝鸡的张福刚。当时,想叫特约中学生编委,时任陕西教育学院院长没有同意,他说成年人叫编委,中学生还是叫编辑吧。
每次去教育学院,我都会提一些刊物,是我平时收集的。我建议丁老师学习人家的长处,特别是装帧设计,希望能洋气一点。我不但当面给丁老师说,还多次写信,但是,却很难改变,一是杂志没有钱请高水平的美术编辑,二是丁老师认为实在一点好。也许这也是刊物的一个风格吧。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丁老师一个人在办这个刊物。作为学生编辑,我力所能及地帮他做一点事。我以杂志的名义约不少人写稿。一九九三年上海首届东亚运动会点燃圣火的“东亚圣女”阎华也回信了。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的童话作家马璇应约寄来了稿子。丁老师还让我以他的名义给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写信,希望他为刊物题词,后来他果然题了词。我也帮着看一些读者来信,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中学生说启功写的“中学生文萃”这几个字不好看,像火柴棍棍。他可能不知道,这正是启功的风格。
我的那些喜欢文学的好朋友,也被我介绍了过来。暑假,我们一起帮丁老师编稿,校对杂志。周盼红住在市二十六中学,他骑自行车过来,进教育学院大门时,没有人提醒他要领一个车牌,等到出门,问他要,他没有,就走不了了。后来只好把车锁到车棚,坐公共汽车回家。他曾办过一份叫《追求》的手抄报,刊首语是他写的,我选登在杂志上。刘峰的一组散文诗《被雨声围困的村庄》也是我编辑的。之前,在学校,我们有过短暂的交流。
我和很多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教育学院。王琪那时候还在陕西第一工业学校上学。张斌峰高考后,来编辑部送稿,他后来做过杂志“心灵之约”栏目的主持人。周盼红也当过一个栏目的主持人,他的笔名叫安达。一九九四年暑假,在编辑部,我们送杨广虎和阎妮一起去北戴河参加文学夏令营。
我们在教育学院的食堂吃饭,晚上就住在编辑部里。铺一张凉席在楼道,几个人躺在一起,凉风吹来,很是惬意,我们经常聊到很晚才睡。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我们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做过报纸编辑和采访工作。在《中学生文萃》的这段经历,应该算是新闻生涯的最开始吧。
上大学后,我和杂志联系越来越少。后来因为报刊整顿,杂志准备停办,我还写过回忆的文章,后来又说可以继续办下去。再后来,丁老师不再担任主编。
杂志早已更换了名字,但是,我们这些人,还是喜欢以《中学生文萃》的名义聚会。时间流逝,如同小学生放学,开始是排着整齐的队伍,人数众多,颇具规模,走着走着,各到各家,长长的队伍变短了。每当想起,难免会有一丝丝的难过,过去的日子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有的人也联系不上了,比如燕怡。我上大学后,他给我寄样刊,给我写信。我记得有一次他为杂志拉到了赞助,写信告诉我,好像自己得到了很大一笔钱,兴奋之情洋溢在纸上。而现在也找不到他了。
去年夏天,弟弟帮我整理堆放在老屋里的那些杂志,其中也有《中学生文萃》,实在太多,他留下了一些,大部分都处理掉了。我感到惋惜,但也不能责备他。回到家,再看当年的杂志,竟然感到有一点点陌生。如此投入地去爱一本杂志,可能只有少年时代才会那么去做,可惜我的少年时代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