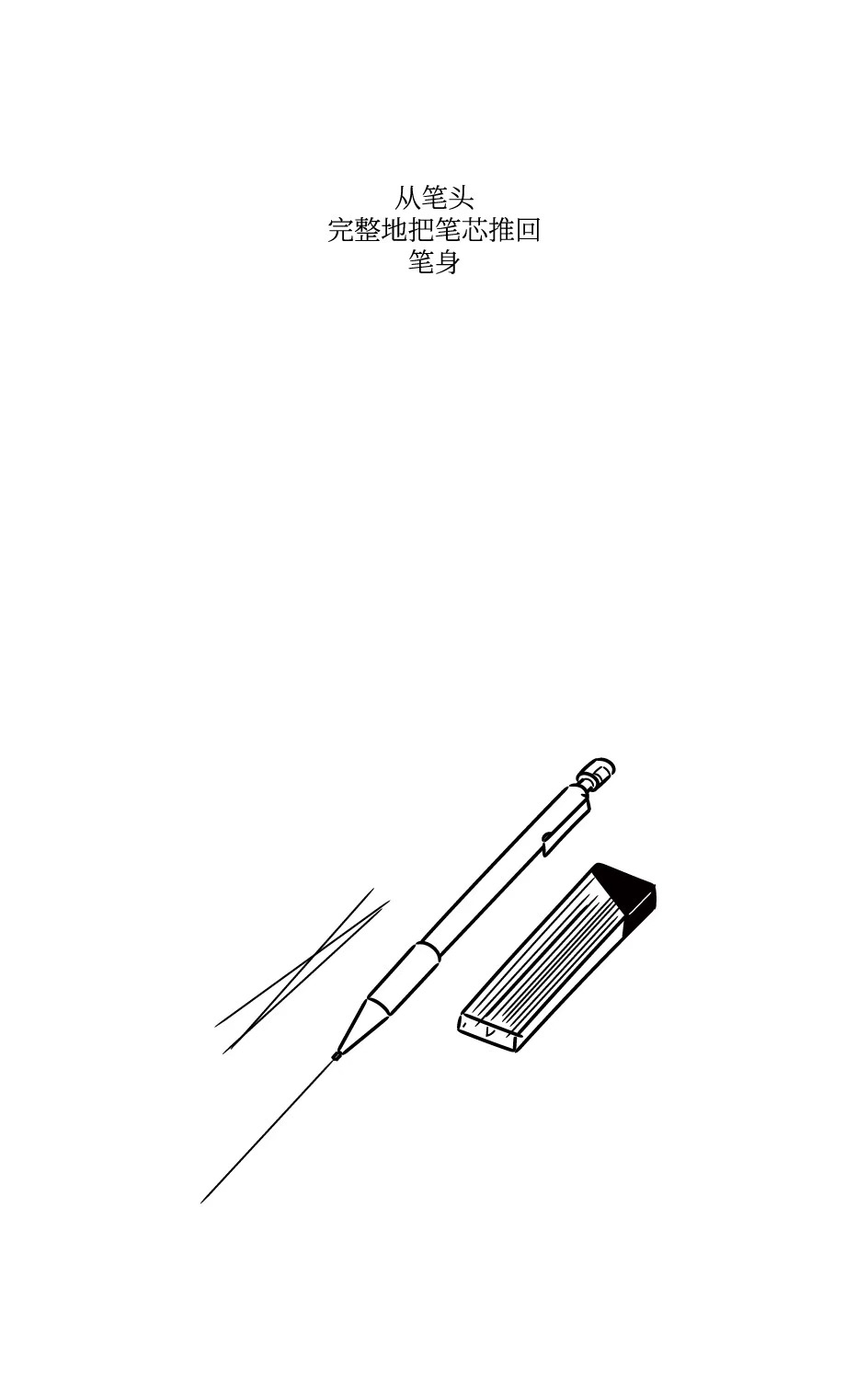汉武帝灭刘氏家三族三万余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
2022-08-08 · 用力答题,不用力生活

‰∏∫‰ªÄ‰πàÈÉΩËإʱâÊ≠¶Â∏ùÊòØÂè≤‰∏äÂî؉∏ĉ∏ĉ∏™Ë¢´ËØõÁÅ≠‰∏âÊóèÁöÑÁöáÂ∏ùÔºåÈöæÈÅì‰∏çÊòØÊØè‰∏™ÁéãÊúùÁöÑÊú´‰ª£ÁöáÂ∏ùÈÉΩË¢´ËØõÁÅ≠‰∏âÊóè‰∫ÜÂêóÔºüËØ¥ÂÆûËØùÂΩìÊó∂ÁúãÂà∞Ëøô‰∏™ÈóÆÈ¢òÊàëËøòÊúâÁÇπÊáµÔºå‰ΩÜÊó¢ÁÑ∂ÊúâÊúãÂèãÈóƉ∫ÜÔºåÈÇ£ÊòäÁ´•Â∞±ÁÆÄÂçïÁöщ∏∫§ßÂÆ∂ÂÅö‰∏™ËߣÈáä„ÄÇËÄåʱâÊ≠¶Â∏ùËøô‰∏™ÂÆåÂÖ®ÊòØËá™ÊÑøÁöÑÔºåËØ¥ÁôΩ‰∫ÜÂ∞±Êò؉ªñ‰∫≤ÊâãËØõÁÅ≠‰∫ÜËá™Â∑±‰∏âÊóèÔºåËÆ≤ÈÅìÁê܉πüÊòØÁãÝÂ≠ó§ö‰∏ÄÁÇπÂïäÔºÅÈÇ£‰πàÈóÆÈ¢òÊù•‰∫ÜÔºåʱâÊ≠¶Â∏ùÈÉΩÊùĉ∫ÜËá™Â∑±ÈÇ£‰∫õ‰∫≤ÊàöÔºåÂèà‰∏∫‰ªÄ‰πà˶ÅËøô‰πàÂÅöÂë¢Ôºü
第一,汉武帝中年的杀戮
河间献王刘德:
ÂàòÂæ∑ÊòØʱâÊôØÂ∏ùÁ¨¨‰∫åÂ≠êÔºåÊØç‰∫≤‰∏∫ʱâÊ≠¶Â∏ùÁîüÊØçÁéã®°ÁöÑÊ≠ªÊïåÊÝóÂߨ„ÄÇÂàòÂæ∑Âú®Ê±âÊ≠¶Â∏ùËøòÊú™ÁôªÂü∫Êó∂Â∞±Â∑≤ÁªèË¢´Â∞ʼn∏∫Ê≤≥Èó¥ÁéãÔºåËÄå‰∏éÂßãËá≥ÁªàÈÉΩÊú™Âç∑Â֕ʱâÊúùÁöÑÊùÉÂäõʺ©Ê∂°„ÄÇÂàòÂæ∑‰∏ÄÁîüÂñúÁà±ÂÑíÂ≠¶ÔºåÊõæÂú®Ê±âÊ≠¶Â∏ù§ßÂäõºòÊâ¨ÂÑíÂÆ∂ÊÄùÊÉ≥Êó∂Âá∫ÂäõËâاö„ÄljΩÜÂêéÊù•ÂõÝÊâÄÂÅöË¥°ÁåƧ™Â§öËÄåºï˵∑ʱâÊ≠¶Â∏ùÁåúÂøåÔºåÊúÄÁªàÈÉÅÈÉÅËÄåÁªà„ÄÇËøôÈáå˶ÅÊèêÂà∞ÔºåÂàòÂæ∑Êú™Ë¢´ÁåúÂøåÂâçË∫´Âº∫‰ΩìÂÅ•Ôºå‰ΩÜË¢´ÁåúÂøåÂê鉪ÖÂõõ‰∏™ÊúàÂ∞±ÂõÝÁóÖÂ骉∏ñÔºåÊúüÈó¥ÂèëÁîü‰∫܉ªÄ‰πà§ßÂÆ∂ÊÉ≥ÂøÖÈÉΩËÉΩÁåúÂà∞ÔºàËøô‰∏™Ëá™ÁÑ∂Êò؉∏çËØ•ÊùÄÁöÑÔºâ„ÄÇ
昭平君陈氏:
Êò≠Âπ≥ÂêõÊòØʱâÊ≠¶Â∏ù‰∏âÂßêÈöÜËôëÂÖ¨‰∏ªÁöÑÁã¨Â≠êÔºåËÄå‰∏îËøò®∂‰∫ÜʱâÊ≠¶Â∏ùÁöщ∫≤•≥ÂÑø§∑ÂÆâÂÖ¨‰∏ª„ÄÇÈôàÊ∞èËá™Âπº‰æøÈ™ÑÁ∫µË∑ãÊâàÔºåÂÖ∂ÊØçÈöÜËôëÂÖ¨‰∏ªÂú®‰∏¥Ê≠ªÂâçÂ∞ܧßÂçäÂÆ∂‰∫ßÊçêÂá∫ÔºåÂè™Ê±ÇÊó•ÂêéʱâÊ≠¶Â∏ùÁúãÂú®Ëá™Â∑±ÁöÑÈù¢Â≠ê‰∏äËÉΩÈ•∂ËøáÊò≠Âπ≥Âêõ‰∏ÄÂëΩ„ÄÇÂêéÊù•Êò≠Âπ≥ÂêõÂõ݉∏∫ÊùÄÊ≠ª‰∫ÜËá™Â∑±ÁöщøùÂßÜËÄåË¢´Âª∑Â∞âÊäìÊçïÔºåÊåâÁêÜËØ¥Êò≠Âπ≥Âêõ‰Ωú‰∏∫ʱâÊ≠¶Â∏ùÁöѧñÁî•ÂäÝ•≥©øÔºåÂ∫îËØ•‰∏牺öÊú⧙§ßË¥£‰ªªÔºå‰ΩÜʱâÊ≠¶Â∏ù‰∏∫‰∫ÜÁª¥ÊåÅÊ≥ïÁ∫™ËøòÊòØÂ∞ÜÊò≠Âπ≥Âêõ§ÑÊ≠ªÔºåÂè™ÊòØÂèØÊÉú‰∫ÜÈöÜËôëÂÖ¨‰∏ªÁöщ∏ÄÁï™Ëã¶ÂøÉÔºàËøô‰∏™Ëá™ÁÑ∂ÊòØËØ•ÊùÄÁöÑÔºâ„ÄÇ
燕王刘定国:
ÂàòÂÆöÂõΩÁöÑÁà∑Áà∑ÊòØʱâÈ´òÁ•ñÂàòÈǶÁöÑÁöÑÂÝÇÂÖѺüÔºåÂõ݉∏∫ÂçèÂä©ÂàòÈǶËç°Âπ≥Èôà˱®Âèõ‰π±‰ª•ÂèäÂ∏ÆÂä©ÈôàÂπ≥Âë®ÂãÉÁ≠â‰∫∫Ê∂àÁÅ≠ËØ∏ÂêïÊúâÂäüÔºåÊâĉª•Ë¢´Â∞ʼn∏∫ÁáïÁéã„ÄÇÂàòÂÆöÂõΩÂú®ÁáïÁéãÁöщΩçÂ≠ê‰∏äÂùê‰∫Ü23Âπ¥ÔºåÊúÄÁªàÂõ݉∏∫±û‰∏ãÂëäÂØÜËÄåË¢´Ê±âÊ≠¶Â∏ù˵êÊ≠ª„ÄÇËøôÈáå˶ÅÊèêÂà∞ÔºåÂàòÂÆöÂõΩÊú¨‰∫∫‰πüÁ°ÆÂÆûËØ•ÊùÄÔºåÂõ݉∏∫‰ªñ•ΩËâ≤ÊàêÊÄßÔºå‰∏ç‰Ω܉∏éÁà∂‰∫≤ÁöѶɴîÊúâÊüìÔºåËÄå‰∏îËøòº∫®∂‰∫ÜÂá݉∏™ÂºüºüÁöѶɴîÔºåÊõ¥‰∏∫ËøáÂàÜÁöÑÊòØԺ剪ñÁ´üÁÑ∂Ëøò‰∏éËá™Â∑±Áöщ∏â‰∏™Â•≥ÂÑøÊúâÊüìÔºàÂàòÂÆöÂõΩÊòØËá™ÊùÄÔºåÂõ݉∏∫ʱâÊ≠¶Â∏ùÂ∑≤Áªè‰∏ã‰∫Ü˵êÊ≠ªÁöÑËØ艪§Ôºâ„ÄÇ
齐厉王刘次景:
Âàòʨ°ÊôØÊòØʱâÈ´òÁ•ñÈïøÂ≠êÂàòËÇ•ÁöÑÊõæÂ≠ôÔºåÂú®ÈΩêÁéãÁöщΩçÂ≠ê‰∏ä‰∏ÄÂÖ±Âè™Âùê‰∫܉∫îÂπ¥„ÄÇËØ¥Êù•‰πü•áÊęԺåË•øʱâÂàùÊúüÁöÑÁöá‰∫≤ÂõΩÊàö‰ºº‰πéÈÉΩÊúâ‰π±‰º¶ÁöÑÁôñ•ΩÔºåÂàòʨ°Êô؉πãÊâĉª•Ë¢´Ê±âÊ≠¶Â∏ù˵êÊ≠ª‰πüÊòØÂõ݉∏∫Ëøô‰∏™„ÄÇÂΩìÂπ¥Âàòʨ°ÊôØÁöÑ•∂•∂Áªô‰ªñÊâæ‰∫܉∏ĉ∏™ÁéãÂêéÔºå‰ΩÜÂàòʨ°Êô؉∏çÂñúʨ¢Ôºå‰∏∫‰∫ÜË°®Á§∫Ëá™Â∑±Áöщ∏çʪ°ÔºåÂàòʨ°ÊôØÁ´üÁÑ∂‰∏éËá™Â∑±Áöщ∫≤ÂßêÂßêÊúâÊüìÔºåËÄå‰∏îÊ≠§‰∫ãËøòË¢´ÂΩìÊó∂ÂÆÝËᣉ∏ªÁà∂ÂÅÉÊâÄÁü•„ÄÇÂàòʨ°ÊôØÂú®ÂæóÁü•Ëá™Â∑±Áöщ∏ë‰∫ãË¢´‰∏ªÁà∂ÂÅɉ∏äÊä•Áªô‰∫ÜʱâÊ≠¶Â∏ùÂêéÔºåÂõ݉∏∫ÊãÖÂøÉʱâÊ≠¶Â∏ùÁöÑÊÉ©ÁΩöÊâĉª•Ëá™Â∞ΩËÄå‰∫°ÔºåËإ˵∑Êù•‰πüÊòØÂ∞¥Â∞¨Áöщ∏çË°åÔºå‰ΩÜÁ©∂ÂÖ∂ÊÝπÊú¨Ê±âÊ≠¶Â∏ù‰πüÂæóËÉåÂçä‰∏™ÈîÖÔºåÂõ݉∏∫ÈÇ£‰∫õÂ𥉪ñÊùÄÁöÑÂàòÊ∞èÁöáÊóèÁ°ÆÂÆû§™Â§ö‰∫Ü
2022-08-11 · 士当弘毅,任重道远。

ÂÖ¨ÂÖÉÂâç92Âπ¥ÂâçÂêéÔºåÂç≥ʱâÊ≠¶Â∏ùÂæÅÂíåÂπ¥Èó¥ÔºåʱâÊúùÁöáÂƧÂÜÖÈÉ®ÂèëÁîü‰∫܉∏ÄÂú∫Ë°ÄËÖ•ÁöѱÝÊùÄÔºåÂâçÂêéÊåÅÁª≠Êï∞Âπ¥„ÄÇÁöáÂêé„Äŧ™Â≠ê„ÄÅÂÖ¨‰∏ª‰ª•ÂèäËØ∏§öË¥µÊàö„ÄŧßËá£ÊÉ®ÈÅ≠Êà≥ÊùÄ„Älj∏éÊ≠§ÂêåÊó∂ÔºåÊÝ™ËøûÊ®™ÁîüÔºåÊï∞‰ª•‰∏áËÆ°ÁîüÁŵ‰∏∫‰πã‰∏ßÁîü„ÄÇÂè≤ËΩΩ‚ÄúÊ∞ëËΩ¨Áõ∏Ëب‰ª•Â∑´ËõäÔºåÂêèËæÑÂ䮉ª•Â§ßÈÄ܉∫°ÈÅìÔºåÂùêËÄåÊ≠ªËÄÖÂâçÂêé‰∏áÊï∞‰∫∫‚ÄùÔºåÊ≠§Âç≥Âè≤Áß∞‚ÄúÂ∑´Ëõä‰πãÁ•∏‚ÄùÁöÑËëóÂêç‰∫㉪∂„ÄÇ
Ê≠§‰∫ãË∑ù‰ªäÂ∑≤‰∫åÂçɉΩôËΩΩÔºå‰∫¶Â¶ÇÂ∞Ū∫ÁöáÂƧÂè∏Á©∫ËßÅÊÉØÁöÑÂÜÖÈÉ®ÂÄæËΩ߉∏ÄÊÝ∑ÔºåÂ∑≤ÊàêËøáÁúºÁÉü‰∫ë„ÄÇÁÑ∂ËÄåÔºå¶ÇÊ≠§Ë°ÄÊ∑ãÊ∑ãÁöщ∏ÄÂú∫Èáç§ßÂéÜÂè≤‰∫㉪∂ÔºåÂú®ÂéÜÊù•Ëß܉∏∫Ê≠£ÁªüÁöÑ„Ääʱâ‰π¶„Äã‰∏≠ÔºåÁ´üÁÑ∂Êï£Ëßʼn∫éÊï∞ÁØáÁ∫™„ÄʼnºÝ‰πã‰∏≠ÔºåÂØ•ÂØ•Êï∞ËØ≠‰∏ÄÂ∏¶ËÄåËøá„ÄÇËøô‰∏çÂæó‰∏ç‰Ωø‰∫∫È°øÁîüÁñëÈóÆÔºö‚ÄúÂ∑´Ëõä‰πãÁ•∏‚ÄùÂèëÁîüÁöÑÂéüÂõÝÊò؉ªÄ‰πàÔºüÂú®ËøôÈ™®ËÇâÁõ∏ÊÆã„ÄÅÁà∂Â≠ê‰∫§ÂÖµÁöÑË°®Ë±°‰πã‰∏ãÔºåÊé©ÁõñÁùÄÁöÑÂÆûË¥®Á©∂Á´üÊò؉ªÄ‰πàÔºü
‚ÄúÂ∑´Ëõä‰πãÁ•∏‚ÄùÂèëÁîüÁöÑÂéüÂõÝ
Ê≠¶Â∏ùÁªüÊ≤ªÊúüÈó¥ÔºåËôΩÁÑ∂ËøôÊó∂Ë•øʱâÁöÑÂõΩÂäõËææÂà∞ÊûÅÁõõÁöÑÈ°∂ÁÇπÔºå‰ΩÜÁ§æ‰ºöÁüõÁõæÂπ∂Ê≤°ÊúâÂõÝÊ≠§ÁºìÂíåÔºåÁõ∏ÂèçÊõ¥ÂäÝÊøÄÂåñ‰∫Ü„ÄÇÂ∞§ÂÖ∂ÊòØÊ≠¶Â∏ùÁªüÊ≤ªÁöщ∏≠„ÄÅÂêéÊúüÔºåÁ∫éÂØπ§ñËøûÂπ¥Áî®ÂÖµÔºåÂØπÂÜÖ§߉∫ãÂÖ¥‰ΩúÔºåÊûŧßÂú∞Ê∂àËÄó‰∫܉∫∫ÂäõÂíåÁâ©ÂäõÔºåÁ©∫ÂâçÂú∞ÂäÝÂâ߉∫܉∫∫Ê∞ëÁöÑË¥üÊãÖ„ÄÇ
Âä݉πãÂÆòÂêèË¥™Êö¥Ôºå˱™Âº∫Ê®™Ë°åÔºåÁÅæËçíȢ뉪çÔºå˵ãÊïõÊóÝÊó∂Ôºå‚Äú‰∫∫Áõ∏È£ü‚ÄùÁöÑÁé∞˱°Â±°Ëßʼn∏çÈ≤úÔºå‚ÄúÁ©∑Ê∞ëÁäØÊ≥ï‚ÄùÁöщ∫㉪∂±ÇÂá∫‰∏çÁ©∑„Älj∏∫‰∫ÜÈïáÂéã‰∫∫Ê∞ëÁöÑÂèçÊäóÔºåÊ≠¶Â∏ùÂèàÈ¢ÅÂ∏ɉ∫ÜËãõÈÖ∑ÁöÑÂàëÊ≥ï„ÄÇËøô‰∫õÊé™ÊñΩÔºåÊõ¥ÂäÝÊøÄ˵∑‰∫∫Ê∞ëÁöÑÂèçÊäó„ÄÇÊ≠¶Â∏ùÁªüÊ≤ªÊú´ÊúüÔºåÂêÑÂú∞Á∫∑Á∫∑ÁàÜÂèëÂÜúÊ∞ë˵∑‰πâÔºåÊçÆ„ÄäÂè≤ËÆ∞¬∑ÈÖ∑Âê艺݄ÄãËΩΩÔºåÂΩìÊó∂Ôºö
‚ÄúÂçóÈò≥ÊúâÊ¢ÖÂÖç„ÄÅÁôΩÊîøÔºåÊ•öÊúâÊÆ∑‰∏≠„ÄÅÊùúÂ∞ëÔºåÈΩêÊúâÂæêÂãÉÔºåÁáï˵µ‰πãÈó¥ÊúâÂùöÂ碄ÄÅËåÉÁîü‰πã±û„ÄǧßÁæ§Ëá≥Êï∞Âçɉ∫∫ÔºåÊìÖËá™Âè∑ÔºåÊîªÂüéÈÇëÔºåÂèñÂ∫úÂ∫ìÔºåÈáäÊ≠ªÁΩ™ÔºåÁºöËæ±ÈÉ°ÂÆàÈÉΩÂ∞âÔºåÊùĉ∫åÂçÉÁü≥Ôºå‰∏∫Ê™ÑÂëäÂéøË∂ãÂÖ∑È£üÔºõÂ∞èÁ槉ª•ÁôæÊï∞ÔºåÊéÝÂ秉π°ÈáåËÄÖ‰∏çÂèØËÉúÊï∞‚Äù„ÄÇ
Â∞±Âú®‚ÄúÂ∑´Ëõä‰πãÁ•∏‚ÄùÁàÜÂèëÁöÑÂâç§ïÔºåÁ´üÊúâ‰∫∫Â∏¶ÂâëÈóØÂÖ•Êàí§áʣƉ∏•ÁöÑÁöáÂÆ´ÔºåË∑ùÊ≠¶Â∏ù‰ªÖÂí´Â∞∫‰πãÈöîÔºåÊ≠¶Â∏ù§ßÊÉ䧱Ëâ≤ÔºåÈ´òÂëºÂç´Â£´‰∏äÂâçÊçâÊãøÔºå‰ΩÜÊù•‰∫∫Âç¥ËΩªÂ∑ßÂú∞ÈÄÉËѱ‰∫Ü„Älj∏∫Ê≠§ÔºåÊ≠¶Â∏ùË∞ÉÂ䮉∏âËæÖș룴ԺåÂ∞ÜÊñπÂúÜÁôæÈáåÁöщ∏äÊûóËãëÂÉèËìñ§¥Âèë‰∏ÄÊÝ∑‚ÄúËìñ‚Äù‰∫܉∏ÄÈÅçÔºåÂèàÂèëÂ∏ÉÊà퉪§ÔºåÂÖ≥Èó≠ÈïøÂÆâÂüéÈó®Âçʼn∏ħ©ÔºåÂπ∂Êå®Èó®ÈÄêÊà∑ËøõË°å§ßÊêúÊçïÔºå‰ΩÜÂßãÁªàÊ≤°ÊúâÊäìÂà∞Ëøô‰ΩçÁ•ûÁßòÁöÑÂâëÂÆ¢„ÄÇËøô‰∏çËÉΩ‰∏çËØ¥ÊòØÂØπÊ≠¶Â∏ùÂøÉÁê܉∏äÁöщ∏ĉ∏™Èáç§ßÂà∫ÊøÄ„ÄÇËøôÁßçÊó•ÁõäÊøÄÁÉàÁöÑÁüõÁõæÂíåÊñó‰∫âÔºåÂ∫îÊòØ‚ÄúÂ∑´Ëõä‰πãÁ•∏‚ÄùÁàÜÂèëÁöÑËøúÂõÝ„ÄÇ
‰∫éÊòØÂêåÊó∂ÔºåÊúùª∑ÂÜÖÈÉ®Êõ¥ÊòØÁüõÁõæÈáçÈáç„ÄÇʱâÂàù‰ª•Êù•Â•âË°åÁöÑȪÑËÄʼnπãÊ≤ªÊâÄÂ∏¶Êù•ÁöÑÂ趉∏ĺäÁóÖÊòØËØ∏‰æØÂùê§ßÔºåÂπ∂ÂõÝÊ≠§ÂغË᥉∫Ü‚Äú‰∏ÉÂõΩ‰πã‰π±‚Äù„ÄÇÊ≠¶Â∏ùÂç≥‰ΩçÂêéÁªßÁª≠Êé®Ë°åÊôØÂ∏ùÁöÑ‚ÄúÂâäËó©‚ÄùÊîøÁ≠ñÔºåÂèàÈ¢ÅÂ∏ɉ∫Ü‚ÄúÊé®ÊÅ©‰ª§‚ÄùÔºå‰ΩøËØ∏‰æØÁéãÁöÑÊùÉÂäõÂíåÈ¢ÜÂú∞Ëøõ‰∏ÄÊ≠•Áº©Â∞èÔºåÁªèʵéÂäõÈáèÊó•ËßÅÂâ亱Ժå‰ΩÜÈöêÊÇ£Âπ∂Ê≤°ÊúâÂΩªÂ∫ïÊÝπÈô§„Älj∏ç‰πÖÔºåÊ∑ÆÂçóÁéãÂÆâÂèõÈÄ܉∫éÂâçÔºåË°°Â±±Áéã˵êË∞ãÂèçÂú®ÂêéÔºåËøô‰∏§Ê¨°Âèõ‰π±ËôΩÁÑ∂ÈÉΩË¢´ÈïáÂéã‰∏ãÂ骄ÄljΩÜÊØèʨ°Âèõ‰π±ÈÉΩ‰∏çÊòØÂ≠§Á´ãÁöÑÔºåÂ∏∏Â∏∏Êò؉∏ä‰∏ãÂëºÂ∫îÔºåÂÜÖ§ñÂãæÁªìÔºåÊâĉª•ÊØèʨ°Âπ≥ÂèõÔºåÂÆûÈôÖÈÉΩÊò؉∏Äʨ°ÊÆãÈÜíÁöѧßÊ∏ÖÊ¥óÔºö
“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千人。”
‰∏∫Âäݺ∫ÂØπÊñáÊ≠¶ÁôæÂÆòÁöÑÊéßÂà∂ÔºåÊ≠¶Â∏ù‰∏ÄÂêëÊòØÊũ®ÅÂÖºÊñΩ„ÄÅÂÑíÊ≥ïÂπ∂Áî®ÁöÑ„ÄljΩÜÈöèÁùÄÊùÉÂäõÁöÑÈ´òÂ∫¶Èõ܉∏≠Ժ剪ñÊÑàÊù•ÊÑàÂàöÊÑéËá™ÁÄÇÂØπ‰∫éÈÇ£‰∫õË߶Áä؉ªñÁöÑÁ¶Å‰ª§ÔºåÊàñ‰ªñËƧ‰∏∫‚Äú‰∏çÂøÝ‚ÄùÁöщ∫∫Ժ剪ñ‰∏çÊÉúÈááÂèñÊàñÂ∫üÊàñÊùÄÔºåÊØ´‰∏çÁïôÊÉÖÔºåÂç≥‰ΩøÂØπÊúùª∑ÈáçËᣉπüÊòضÇÊ≠§„ÄÇ
ÁªàÊ≠¶Â∏ù‰πã‰∏ñÔºåÂâçÂê鉪ªÁõ∏Âçʼn∏â‰∫∫ÔºåÂÖ∂‰∏≠Áß∞Âæó‰∏äÂØøÁªàÊ≠£ÂØùÁöÑÂØ•ÂØ•ÊóÝÂáÝÔºåËÄåË¢´ÈĺËá™ÊùÄ„ÄÅÁã±Ê≠ªÊàñËÖ∞Êñ©ÁöÑÁ´üÊúâÂÖ≠‰∫∫„ÄÇÈöæÊÄ™ÂÖ¨Â≠ôË¥∫Ë¢´‰ªªÂëΩ‰∏∫Á¨¨Âçʼn∏ĉªªÂûÇÁõ∏Êó∂Ժ剪ñ‰∏牪ÖÊ≤°Êúâ‰∏ÄÁÇπÁÇπÈ´òÂÖ¥ÁöÑË°®Á§∫ÔºåÁõ∏Âèç‚ÄúÈ°øȶñÊ∂ïÊ≥£‚ÄùÔºå‰∏çÂèóÂç∞Áºì„ÄÇÂΩìËø´‰∏çÂæóÂ∑≤ÔºåÊúÄÂêéÊé•ÂèóÊó∂Ժ剪ñÂá∫Èó®Âç≥‰ª∞§©ÈïøÂèπÈÅìÊÄßÂëΩÈöæ‰øù„ÄÇÂêéÊù•Ôºå‰ªñÊûúÁÑ∂Ê≠ª‰∫éÁ㱉∏≠„ÄÇÊ≠¶Â∏ùËøôÁßçÂñúÊÄ퉪ªÊÉÖÔºåÂàëÊùÄÊóÝÂøåÁöÑÂÅöÊ≥ïºï˵∑ÊúùËá£Ê∑±Ê∑±ÁöÑÂøßÊÉßÂíå‰∏çʪ°Ôºå‰∏∫Ê≠§ÔºåÊ≠¶Â∏ùÂèàÊé®Ë°å‚ÄúËÖπËØΩÊ≥ï‚ÄùÔºå§ßËᣂÄú‰∏çÂÖ•Ë®ÄËÄåËÖπËØΩÔºåËÆ∫Ê≠ª‚ÄùÔºåËøôÊó∂Ê≠¶Â∏ùÂ∑≤ÁªèÂè™Ë¶Å•¥ÊâçÔºå‰∏ç˶ʼn∫∫Êâç‰∫Ü„ÄÇÊ≠§ÂêéÔºå‚ÄúÂÖ¨Âçø§ß§´Â§öËØåË∞àÂèñÂÆπÁü£‚ÄùÔºåËÄåÂÖ∂‰∏≠ÊúÄÁ™ÅÂá∫Áöщ∫∫Áâ©ÊòØʱüÂÖÖ„ÄÇ
Ê≠¶Â∏ùÊôöÂπ¥ÔºåÂƴª∑ÁüõÁõæÁöÑÁѶÁÇπÈõ܉∏≠Âú®Áî±Ë∞ÅÊù•ÁªßÊâøÁöá‰ΩçÁöÑÈóÆÈ¢ò‰∏ä„ÄÇÊ≠¶Â∏ùÂÖ±ÊúâÂÖ≠Â≠êÔºåÈïøÂ≠êÊçÆÁ≥ªÂç´ÁöáÂêéÊâÄÁîüÔºåË¢´Á´ã‰∏∫§™Â≠êÔºå‰ΩÜÊ≠¶Â∏ù´åÊÅ∂§™Â≠êÔºåÂç´ÂêéÂèàÂõÝÂπ¥ËÄÅËâ≤Ë°∞§±ÂÆÝÔºåÁöáÂêéÂí姙Â≠êÁöÑÂú∞‰ΩçÂèëÁîüÂä®ÊëáÔºåÊâĉª•ÔºåÂÆ´‰∏≠Èô§‰∫ÜÂ∑≤ÁªèÂΩ¢ÊàêÁöÑÂ∏ùÂÖöÂí姙Â≠êÂÖö§ñÔºåÂÖ∂‰ΩôÂêÑÂ≠êÂá݉πéÈÉΩÊúâËá™Â∑±Áöщ∏ÄÊ¥æÂäøÂäõÔºåÂΩºÊ≠§ÂãæÂøÉÊñóËßíÔºåÊöó‰∏≠±ïºÄÂØπÁöá‰ΩçÁöÑËßíÈÄê„ÄÇ
Èò¥ËÑ∏Áã°ËØàÁöÑʱüÂÖÖÂØπÊ≠§Ê¥ûËã•ËßÇÁÅ´Ôºå‰∏∫ÁåéÂèñ‰∏™‰∫∫ÁöÑËç£ÂçéÂØåË¥µÔºå‰ªñ‰∏çÊÉú‰ª•ÂæóÁΩ™Â§™Â≠êÊù•ËƮ•ΩÊ≠¶Â∏ù„ÄÇÂú®‰ªñÊãÖ‰ªªÁõ¥ÊåáÁª£Ë°£‰ΩøËÄÖÈö艪éÊ≠¶Â∏ùÂéªÁîòÊ≥âÂÆ´Êó∂Ôºå‚ÄúÈĢ§™Â≠êÂÆ∂‰Ωø‰πòËΩ¶È©¨Ë°åÈ©∞ÈÅì‰∏≠‚ÄùÔºåÂéªÈóÆÂÄôÊ≠¶Â∏ù˵∑±քÄÇÈ©∞ÈÅìÊòØÂæ°Áî®ÁöÑԺ姙Â≠ê‰ΩøËÄÖ˵∞ËøôÊù°Ë∑ØÊòØ‚ÄúÁäØÁ¶Å‚ÄùÁöÑÔºåʱüÂÖÖÂΩìÂç≥Êâ£Áïô‰∫ܧ™Â≠êÁöÑËΩ¶È©¨Ôºå§™Â≠êÊ¥æ‰∫∫Âê뉪ñʱÇÊÉÖÔºåÂπ∂ÂÜç‰∏â§ÆÂë䉪ñ‰∏ç˶ÅËÆ©Ê≠¶Â∏ùÁü•ÈÅìËøô‰ª∂‰∫ãÊÉÖÔºåʱüÂÖÖ‰∏çÂê¨ÔºåÂéüÂéüÊú¨Êú¨ÂêëÊ≠¶Â∏ù‰Ωú‰∫ÜʱáÊä•ÔºåÊ≠¶Â∏ùÂØπÊ≠§Â§ßÂäÝ˵û˵èÔºåËØ¥‚Äú‰∫∫Ëá£ÂΩì¶ÇÊòØÁü£„ÄÇ‚ÄùʱüÂÖÖÂõÝÊ≠§‚Äú§ßËßʼnø°Áî®Ôºå®ÅÈúá‰∫¨Â∏à‚ÄùÔºå‰Ω܉πü‰∏駙Â≠êÁªì‰∏ã‰∫܉ªáÊÄ®„ÄÇÊúùª∑ÂÜÖÈÉ®‰∫íÁõ∏ÂÄæËΩßÔºåÂõõÂà܉∫îË£ÇÔºåÂ∫î‰∏∫‚ÄúÂ∑´Ëõä‰πãÂ∞ö‚ÄùÁàÜÂèëÁöÑËøëÂõÝ„ÄÇ
Ê≠§Â§ñÔºåʱâÊúùÁöáÂ∏ùÊó݉∏ĉ∏çËø∑‰ø°ÔºåËÄåʱâÊ≠¶Â∏ùÂèàÊòØÂÖ∂‰∏≠ÊúÄËø∑‰ø°Áöщ∏ĉ∏™„Äljªñ‰ªé‰∫ãÁ•≠Á•ÄÁöÑËßÑÊ®°Êúħ߄ÄÅʨ°Êï∞ÊúħöÔºå‰∏î§öʨ°‰∫≤Ëá™ÂéªÊ≥∞±±‚ÄúÂ∞ÅÁ¶Ö‚ÄùÔºåËøôÂú®Âé܉ª£Â∏ùÁéã‰∏≠Êò؉ªÖËßÅÁöÑ„ÄÇ
汉武帝迷信最突出的表现是求神仙。他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对方士言听计从,多次上当受骗。他起先是礼神君、祀灶,继而听信李少君的话派方士入海求神仙,后来又封献鬼神方的骗子少翁为文成将军。汉武帝最荒唐的莫过于把一个以神仙使者自命的方士大封为食邑二千户的乐通侯,“赐列汉甲第、僮千人”,甚至把女儿嫁给了他。可见,汉武帝迷信中毒之深,已达到至死不悟的程度。
Êó¢ÁÑ∂ÂØπ‚ÄúÊñπ£´Âè؉ª•Ëá¥Á•û‚Äù¶ÇÊ≠§Á¨É‰ø°‰∏çÁñëÔºåÈÇ£‰πàÂØπ‚ÄúÂ∑´ËõäÂè؉ª•Êùĉ∫∫‚ÄùÊõ¥ÊòØÊ∑±‰ª•‰∏∫ÁÑ∂‰∫Ü„ÄÇÂõÝÊ≠§ÔºåʱâÊ≠¶Â∏ùÂØπË°å‚ÄúËõä‚ÄùËÄÖÊ∑±ÊÅ∂ÁóõÁªùÔºå‰∏ÄÁªèÊü•Âá∫Ôºå‰∏•ÊÉ©‰∏çË¥∑„ÄÇÂõÝÊùÜÂ∞ÜÂÜõÂÖ¨Â≠ôÊïñÂç≥‚ÄúÂù궪‰∏∫Â∑´Ëõä‚ÄùË¢´ÊùÄÔºõÂÆ´‰∏≠‚ÄúÊçï‰∏∫Â∑´ËõäËÄÖÔºåÁöÜÊû≠ȶñ‚ÄùÔºåÈôàÁöáÂêéÂõݶíÂøåÂç´Â≠꧴ÂæóÂÆÝÔºåË°å‚ÄúÂ∑´ËõäÁ•ÝÁ•≠Á•ùËØÖ‚ÄùÂç´Â≠꧴ԺåÁªìÊûúË¢´Â∫üÔºå‚ÄúÁõ∏ËøûÂèäËØõËÄÖ‰∏âÁôæ‰Ωô‰∫∫‚Äù„ÄÇ
ʱâÊ≠¶Â∏ùÊôöÂπ¥ÔºåË∫´‰Ωì§öÁóÖÔºå‚ÄúÊÑè§öÊâÄÊÅ∂Ժ剪•‰∏∫Â∑¶Âè≥Áö܉∏∫ËõäÈÅìÁ•ùËØÖ‚ÄùÂäÝÂÆ≥Ëá™Â∑±Ôºå‰ªñËøôÊó∂‰∏牪ÖÂØπË∫´ËæπÁöщ∫∫‰∏ç‰ø°‰ªªÔºåÂØπËá™Â∑±ÁöѶªÂ≠êÂÑø•≥‰πüÂêåÊÝ∑ÊÄÄÁñë„ÄÇʱâÊ≠¶Â∏ùÊÝπÊ∑±ËíÇÂõ∫ÁöÑËø∑‰ø°ÊÄùÊÉ≥ÔºåÂ∫î‰∏∫‚ÄúÂ∑´Ëõä‰πãÁ•∏‚ÄùÁàÜÂèëÁöÑÂÜÖÂõÝÔºå‰∏îÂØπ‚ÄúÂ∑´Ëõä‰πãÁ•∏‚ÄùÂ∫îË¥ü‰∏ªË¶ÅË¥£‰ªª„ÄÇ
Âú®‰ª•‰∏äÂêÑÂõÝÁ¥ÝÁöÑÊ鮉∏≠‰πã‰∏ãÔºåÁªà‰∫é‰∏ÄÂú∫Áî±Ê±âÊ≠¶Â∏ù‰∫≤Ëá™ÂغʺîÁöÑÔºåÊãøËá™Â∑±È™®ËÇâºÄÂàÄÁöÑÊÇ≤ÂâßÊè≠ºĉ∫ÜÂ∫èÂπï„ÄÇ
巫蛊之祸掩盖的正是皇室内部乃至整个朝廷内外的权力斗争
ÈïøÊúüÊù•ÔºåÊ≠¶Â∏ù‰∏ÄÁõ¥ÂØπÂç´Ê∞èÈõÜÂõ¢Â≠òÂú®Êàí§á‰πãÂøÉÔºåËìÑË∞ãÂ∑≤‰πÖÔºå˶ÅÈì≤Èô§Âç´Ê∞èÈõÜÂõ¢ÂØπÁöá‰ΩçÁöÑ®ÅËÉÅ„ÄÇÂè™ÊòØÁ¢ç‰∫éÂØπÂåà•¥ÁöÑÊàò‰∫ãÊú™Âπ≥ÔºåÊóÝÊ≥ïÂä®Êâã„ÄÇÂà∞ÂæÅÂíåÂπ¥Èó¥ÔºåÂêÑÂú∞Êàò‰∫âÂùáÂëäÁªìÊùü„ÄÇÈïø‰πÖÁöÑÊàò‰∫âºÄÊîØÔºåÂä≥Ê∞뉺§Ë¥¢ÔºåÂõΩÂäõË¥¢ÂäõÂùáÂ∑≤‰∏çÂÖÅËÆ∏ÂÜçÁª¥ÊåÅÂ∫û§ßÁöÑÊàò‰∫âË¥πÁÄÇÂÜçÂä݉∏äÊ≠§Êó∂Ê≠¶Â∏ùÂ∑≤Âπ¥ËÄŧöÁóÖÔºåÁªßÂó£ÈóÆÈ¢òÂ∑≤Âઉ∏çÂÆπÁºì„ÄÇËÄå‰∏îÂç´Ê∞èÈõÜÂõ¢ÁöÑÈáç˶ÅÊîØÊü±Âç´ÈùíÂ∑≤ÁªèÂ骉∏ñÔºåÂç´Ê∞èÈõÜÂõ¢Áöщ∏çÂ∞ëÊàêÂëòÂ∑≤Áî±Ê≠¶Â∏ùÈÄöËøáÂêÑÁßçÊâãÊƵÊàñÊ≤ªÁΩ™ÔºåÊàñÂÖçËÅå„ÄÇ
ÂõÝÊ≠§ÔºåÂç´Ê∞èÈõÜÂõ¢Ê≠§Êó∂ÊóÝËÆ∫‰ªéÂäøÂäõÊàñ‰∫∫Êï∞‰∏äÔºåÈÉΩÂ∑≤‰∏ç¶ÇÂç´ÈùíÂú®Êó∂ÈÇ£ÊÝ∑ÁÇôÊâãÂèØÁÉ≠‰∫Ü„ÄÇÂú®Êúùª∑‰∏≠ÔºåÂõÝ‚ÄúÂç´ÈùíËñ®ÔºåËᣉ∏ãÊóݧç§ñÂÆ∂‰∏∫ÊçÆÔºåÁ´üʨ≤Êûѧ™Â≠ê‚Äù„ÄÇÁø¶Èô§Âç´Ê∞èÈõÜÂõ¢ÁöÑÊó∂Êú∫Â∑≤Âà∞Ôºå‰∫éÊò؉∏ÄÂú∫Áî±Ê≠¶Â∏ù‰∫≤Ëá™ÂغʺîÁöÑÔºåÊãøËá™Â∑±È™®ËÇâºÄÂàÄÁöÑÊÇ≤ÂâßÊè≠ºĉ∫ÜÂ∫èÂπïÔºåÂÆÉÁöÑÂâç•èÂç≥ÊòØËøôÂú∫Áî±Èü©ËØ¥„ÄÅʱüÂÖÖÁ≠âÂà∂ÈÄÝÁöÑ‚ÄúÂ∑´Ëõä‰πãÁ•∏‚Äù„ÄÇ
Ê≠¶Â∏ù‰∏ÄÊñπÈù¢ÂëΩ‰ª§Èü©ËØ¥„ÄÅʱüÂÖÖ‰ª•Ê≤ªËõä‰∏∫ÂêçÔºåÂ∞ÜÁ•∏Ê∞¥ÂºïÂêëÁöáÂêé„Äŧ™Â≠êÔºõÂ趉∏ÄÊñπÈù¢Ëá™Â∑±ÊâòÁóÖÁ¶ªÂºÄ‰∫¨Âüé„Äǧ™Â≠ê„ÄÅÁöáÂêéÂèäÂÆ∂Âêè‚ÄúËØ∑ÈóÆÁö܉∏çÊä•‚ÄùÔºå‰Ωø§™Â≠ê‚ÄúÊó݉ª•Ëá™Êòé‚Äù„ÄÇÈĺËø´Â§™Â≠ê˵∑ÂÖµÊùÄÈü©ËØ¥„ÄÅʱüÂÖÖÔºåÂ∞ÜÂÖ∂ÁΩƉ∫é‚ÄúË∞ãÂèç‚Äù¢ÉÂú∞Ժ剪•Ë᥂ÄúÈïøÂÆâ‰∏≠Êâ∞‰π±Ôºåˮħ™Â≠êÂèç‚Äù„Älj∫éÊòØÔºåÊ≠¶Â∏ùÂêçÊ≠£Ë®ÄÈ°∫‰∏ãËØèÔºö
“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ÊúÄÁªàԺ姙Â≠êË¢´ÁΩƉ∫éÂøÖÊ≠ª‰πãÂú∞„ÄÇÊ≠§ÂêéÔºåÂèàÈÄöËøáËøûÂùêÊ≤ªÁΩ™ÔºåÁöáÂêéÔºåÂÖ¨‰∏ªÁ≠âÂùáË¢´Â∫üȪúËØõÊ≠ª„ÄÇËá≥Ê≠§ÔºåÊ≠¶Â∏ù‰∏ÄÊâãÂà∂ÈÄÝÁöÑ‚ÄúÂ∑´Ëõä‰πãÁ•∏‚ÄùÁõÆÁöÑÂÖ®ÈÉ®ËææÂà∞Ôºö§™Â≠êÂàòÊçÆË¢´ÊùÄÔºåÊòìÂó£Â∑≤ÊàêÂÆö±ÄÔºõÂç´Ê∞èÈõÜÂõ¢ÂÖ®ÈÉ®Áø¶ÁÅ≠„ÄÇËá™Âç´Â≠꧴„ÄÅÂç´ÈùíÊòæË¥µ‰ª•Êù•ÔºåÈïøÊúüÂéãÂú®Ê≠¶Â∏ùËÉ∏‰∏≠ÁöÑÂøÉÁóÖÁªà‰∫éÈô§Â骄ÄÇ
‰ªéÊ≠§Ê≠¶Â∏ùÂç≥ÂèØÊåâËá™Â∑±ÁöÑÊÑèÊÑøÔºåÈáçÊñ∞Á°ÆÁ´ãËá™Â∑±ÁöÑÁªßÊâø‰∫∫„ÄÇÊ≠¶Â∏ùÊó∂ÊúüÁöщ∏≠ÂõΩÁ§æ‰ºöÔºåÊ≠£Â§Ñ‰∫éÂ∞Ū∫Á§æ‰ºöÁöÑÂàùÊúüÔºå§߉∏ÄÁªüÁöÑÂ∞Ū∫‰∏ìÂà∂ÁªüÊ≤ªËøòÂàöÂàöÂΩ¢ÊàêÔºåÂõÝÊ≠§ÂøÖÁÑ∂‰∏éÂÆɉπãÂâçÁöÑÁ§æ‰ºöÂΩ¢ÊÄÅÊúâÁùÄÂçɉ∏ù‰∏áÁºïÁöÑËÅîÁ≥ª„ÄÇÊóÝËÆ∫ÊòØÂΩìÊó∂ÁöÑÁ§æ‰ºöÁªèʵé„ÄÅÊîøÊ≤ªÂà∂Â∫¶ÔºåËøòÊòØÊÑèËØÜÂΩ¢ÊÄʼn∏≠ÔºåÈÉΩÊ∑±ÂàªÂú∞ÂèçÊòÝÂá∫Ëøô‰∏ÄÂéÜÂè≤ÁöÑÈÅóËøπ„ÄÇÁâπÂà´ÊòØÂ뮉ª£‰ª•Êù•ÂΩ¢ÊàêÁöÑÂÆ∂ÊóèÂÆóÊ≥ïÂà∂Â∫¶ÔºåÊõ¥ÊòØÁäπ¶ÇÂçÉÂπ¥Âè§Ëó§‰∏ÄËà¨ÔºåÁõòÊÝπÈîôËäÇÂú∞ÁºÝÁªïÁùÄË•øʱâÁ§æ‰ºö„ÄÇÂ∞ΩÁÆ°Á§æ‰ºöÂà∂Â∫¶„ÄÅÁîü‰∫ßÂÖ≥Á≥ªÂ∑≤ÂèëÁîü‰∫ÜÂèòÂåñÔºå‰Ω܉Ωú‰∏∫Á§æ‰ºöÁªÑÁªáÂΩ¢ÊÄÅÂü∫Á°ÄÁöÑÂÜÖÊ∂µÂÆûË¥®ÔºöÂÆ∂ÊóèÂÆóÊ≥ïÂà∂Â∫¶ÔºåÂç¥Âπ∂Êú™ÂõÝÊ≠§ËÄåÂèòÂåñ„ÄÇÁõ∏ÂèçÔºåÂÆÉÂ祉∏ÄÁõ¥ÊòØÊ雷∏™‰∏≠ÂõΩÂ∞Ū∫Á§æ‰ºö˵ñ‰ª•Áª¥ÊåÅÁöÑÂü∫Á°Ä„ÄÇÂú®Ë•øʱâÊó∂‰ª£ÔºåÂ∞èÂà∞‰∏ĉ∏™ÂÆ∂ÊóèÔºå§ßÂà∞‰∏ĉ∏™ÊùëËêΩ„ÄÅÂå∫ÈÇëÔºåÂú®Â∞Ū∫Ë°åÊîøÊú∫ÊûÑË°®Ë±°‰πã‰∏ãÁöÑԺ剪çÁÑ∂Êò؉ª•ÂßìÊ∞èË°ÄÁºò‰∏∫Á∫ΩÂ∏¶ÁöÑÂÆ∂ÊóèÂÆóÊ≥ïÂà∂Â∫¶„ÄÇ
Âú®Â∞Ū∫ÁöáÂƧÂÜÖÈɮԺåÁöáÂ∏ùÊâÄ˶ÅÁª¥ÊåÅÁöÑÔºåÂè™ÊòØËá™Â∑±‰∏ÄÂßìÁöÑÂÆ∂§©‰∏ãÔºåʱü±±Á§æÁ®∑Âè™ÊòØÂ∞Ū∫ÂõΩÂÆ∂Áöѧñ£≥ÔºåËÄåÂÖ∂ÊÝ∏ÂøÉÔºåÂàôÊò؉ª•ÁöáÂ∏ù‰∏∫ȶñÁöщ∏ÄÂßìÂÆ∂Êóè„ÄÇÊïÖÁ߶ÂßãÁöáÁªü‰∏ĉ∏≠ÂõΩÂêéÁ´ãÂç≥ËÄÉËôëÁöÑÊò؉∏á‰∏ñ‰∏çÊòìÁöÑ˵¢Ê∞èʱü±±„ÄÇËÄåÂàòÈǶ§∫ÂèñÁöá‰ΩçÂêéÔºåȶñÂÖàÊÉ≥ÁöщπüÊòØ‚ÄúÈùûÂàòÊ∞èËÄåÁéãԺ姩‰∏ãÂÖ±ËØõ‰πã‚Äù„ÄljΩïÂܵÈõÑÊâç§ßÁï•ÁöÑʱâÊ≠¶Â∏ùÔºåÊõ¥ÂÆπ‰∏çÂæó‰ªñ‰∫∫‰∏éÂÖ∂ÂÖ±‰∫´Ëá≥Â∞äÊùÉÂäõ„ÄÇ
‰ΩÜÊòØԺ剪çÈ°ªÁúãÂà∞ÂÆ∂ÊóèÂÆóÊ≥ïÂà∂Â∫¶Âà∞‰∫ÜÁ߶ʱâÊó∂ÊúüÔºåÁ∫éÂ∞Ū∫‰∏ìÂà∂ÈõÜÊùÉÂà∂Â∫¶ÁöÑÂèë±ïÔºåÂÆÉÊâÄËÉΩ˵∑ÁöщΩúÁ∏éÊïàËÉΩÔºåÈÄêÊ∏ê‰∏ãÈôçÂà∞Á§æ‰ºöÁöщ∏≠‰∏ã±ÇÔºåÊàê‰∏∫Â∞Ū∫ÊîøÂ∫úÁª¥Êä§Âú∞ÊñπÁªüÊ≤ªÁöÑÊâãÊƵ‰πã‰∏Ä„ÄÇËÄåÂú®Á§æ‰ºöÁöщ∏ä±ÇÔºåË¥µÊóèÈõÜÂõ¢„ÄÅÁöáÂƧÂÜÖÈɮԺåÂÆ∂ÊóèÂÆóÊ≥ïÂà∂ÁöщΩúÁî®Ë∂äÊù•Ë∂äÂá躱ԺåÊõ¥Â§öÁöÑÂè™Êò؉øùÁïôÂÖ∂Ë∫Ø£≥ÔºåÂú®ÁöáÂƧÂÜÖÈÉ®ÁúüÊ≠£Ëµ∑‰ΩúÁî®ÁöÑÂàôÊò؉ª•ÈõÜÂõ¢Âà©Áõä‰Ωú‰∏∫ÂèñËàçÊÝáÂáÜ„ÄÇ
Âú®Ë•øÂë®ÂΩ¢ÊàêÁöщª•Ë°ÄÁºò‰∏∫Âü∫Á°ÄÁöÑÂÆ∂ÊóèÂÆóÊ≥ïÂà∂ÔºåÂÆÉÊâÄÁª¥Á≥ªÁöÑÊò؉∏•ÊݺÁöÑ´°ÈïøÂà∂„ÄljΩú‰∏∫ÈïøÂ≠êԺ剪ñÊâÄÂ∫îÊúâÁöÑÂú∞‰ΩçÂíåÊùÉÂà©ÔºåÊò؉∏çÂÆπ‰ªª‰Ωï‰∫∫ÊèêÂá∫ºÇËÆÆÁöÑ„ÄÇÁÑ∂ËÄåÂà∞‰∫ÜÁ߶ʱâÊó∂ÊúüÔºåÂ∏ùÁéã‰∏∫‰∫ÜÁª¥Êä§ÂÖ∂‰∏™‰∫∫Áöщ∏ìÂà∂ÁªüÂà∂Ժ剪•Âè䉪ñÊú¨‰∫∫‰∏∫‰ª£Ë°®ÁöÑÊîøÊ≤ªÈõÜÂõ¢ÁöÑÂà©ÁõäÔºå‰∏çÊÉúÊâìÁÝ¥Ëøô‰∏™Á•ñÂÆóÁïô‰∏ãÁöÑÊàêÊ≥ï„ÄǶÇÁ߶ÊúùÂ∞±Â∫ü§™Â≠êÊâ∂ËãèËÄåÁ´ãËÉ°‰∫•„ÄÇÂõÝÊ≠§ÔºåÂΩìÊ≠¶Â∏ùÁúãÂà∞§™Â≠ê‚Äú‰∏çÁ±ªÂ∑±‚ÄùÔºå‰∏çËÉΩË¥ØÂΩªËá™Â∑±ÁöÑÊîøÊ≤ªÊä±Ë¥ü‰πãÊó∂Ժ剪ñÂøÖÁÑ∂‰∏牺öÂõÝ´°ÈïøÂà∂ËÄåÊùüÁºöÊâãËÑöԺ姙Â≠êÊòì‰∫∫‰πüÂ∞±Âú®ÂøÖÁÑ∂‰πã‰∏≠‰∫Ü„ÄÇ
ÂõÝÊ≠§ÔºåÂΩì‰∏ĉ∏™ÂÆ∂ÊóèÊàê‰∏∫ÂÖ®ÂõΩÁöÑȶñÂßìÔºåÂÆÉÁöщª£Ë°®ËÄÖÊàê‰∏∫Ëá≥Â∞äÊó݉∏äÁöÑÂ∏ùÁéã‰πãÊó∂Ôºå‰Ωú‰∏∫ÂÆ∂ÊóèÂà©ÁõäÁöщª£Ë°®ËÄÖ‚Äî‚ÄîÁöáÂ∏ùԺ剪ñȶñÂÖàËÄÉËôëÁöÑÂàôÊòضljΩï‰ΩøÂõΩÂÆ∂‚Äî‚Ä‰∏ã„ÄÅʱü±±„ÄÅÁ§æÁ®∑‚Äî‚ÄîÂßãÁªàÁª¥Á≥ªÂú®ËÉΩ‰ª£Ë°®Ëá™Â∑±Âà©ÁõäÁöÑÊîøÊ≤ªÈõÜÂõ¢Êâã‰∏≠„ÄÇÊóÝËÆ∫Á߶ÂßãÁöáÔºåËøòÊòØʱâÊ≠¶Â∏ùÔºåÈÉΩÊòضÇÊ≠§„ÄÇÊ雷∏™ÂõΩÂÆ∂Êú∫Âô®„ÄÅË°åÊîøËÆæÊñΩ„ÄÅÊîøÁ≠ñÊ≥§„ÄÅÂÜõÈòüÁõëÁã±ÔºåÂÖ∂ȶñ˶ÅËÅåË¥£Âç≥‰∏∫‰øùÂç´‰ª•ÁöáÂ∏ù‰∏∫ȶñÁöÑÈÇ£‰∏™ÊîøÊ≤ªÈõÜÂõ¢ÁöÑÂà©ÁõäÔºåÂπ∂‰Ωø‰πãÂæ󉪕ª∂Áª≠ÔºåÊ≠§Âç≥‚Äú‰∏á‰∏ñ‰∏çÊòì‰πãʱü±±‚Äù„ÄÇÂéÜÊù•ÁöÑÂ∏ùÁéã‰πãË∑ØÔºåÊóݧñ‰πéÊ≠§ÔºåÊ≠§Ë∞ìÊàêÂ∏ù‰∏ö‰πãÂ∏∏ÈÅì„ÄÇ
Âà∞Ë•øʱâ‰∏≠ÊúüÔºåÁªèËøáʱâÊ≠¶Â∏ùÁöÑÊñáÊ≤ªÊ≠¶ÂäüÔºå§ñÈÉ®ËÉΩ‰∏é‰πãÊäóË°°ÁöÑÊïåÂõΩÊàñÂÜõ‰∫ãÈõÜÂõ¢ÔºåÂ∑≤‰∏çÂ≠òÂú®ÔºõËÄåÂú®Âº∫§ßÁöÑÂ∞Ū∫ÂõΩÂÆ∂Êú∫Âô®„Äʼn∏ìÂà∂ÈõÜÊùÉÁöÑÁªüÊ≤ª‰∏ãÔºåÂÜÖÈÉ®Âå∫Âå∫‚ÄúÂ∞èÊ∞ë‚ÄùÈÄÝÂèçÔºåÊõ¥Êò؉∏çËÉΩÊéÄ˵∑È£éʵ™„ÄÇÂõÝÊ≠§ÔºåÁâπÂà´ÊòØÂà∞‰∫ÜÊ≠¶Â∏ùÊôöÂπ¥Ôºå‰ªñËÄÉËôëÂæóÊúħöÁöÑÔºå‰πüÊòØÊ∑±ÊÑüÂøßËôëÁöÑÔºåÂ∞±ÊòØÊù•Ëá™ÁöáÂƧÂÜÖÈÉ®ÁöÑËêߢô‰πã‰π±„Äǧ™Â≠êÂàòÊçÆÔºåÈïøÊúü§щ∫éÊØçÂÖöÁöÑÂΩ±Âìç‰πã‰∏≠ÔºöÂç´ÁöáÂêé‚Äî‚ÄÂ≠ê‚Äî‚ÄîÂç´ÈùíÔºåÂπ∂Áî±Ê≠§ÂΩ¢ÊàêÁöÑÂç´Ê∞èÈõÜÂõ¢‚ÄúÈú∏§©‰∏ã‚ÄùÔºåÂ∑≤‰∏∫‰∏ñ‰∫∫Áû©ÁõÆ„ÄÇÁâπÂà´ÊòØÈÄöËøáÈü©ËØ¥‰Ωú‰∏∫ÂÜÖÁ∫øÔºåÊ≠¶Â∏ùÂØπÂç´Ê∞èÈõÜÂõ¢ÁöÑÂÜÖÂπïÔºåÊõ¥Êò؉∫ܶÇÊåáÊéå„ÄÇÈõÑÊâç§ßÁï•ÁöÑʱâÊ≠¶Â∏ùÔºåÂÖ∂‰∏™ÊÄßÊòØËá≥Â∞äÁã¨Â§ÑÔºåÂØπÊúùª∑§ßËᣄÄÅÂ∞ÜÂ∏ÖÂøÖÊÅ©‰ªéÂ∑±Âá∫„ÄǶÇËãèª∫ÊõæÂäùÂç´ÈùíÊãõË¥§Â֪£´Ôºå‰ΩÜÂç´ÈùíÂàôË®ÄÔºö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招贤黜不肖者,人主自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可见卫青深知其主。武帝对大臣将帅如此,对自己的继承人太子更是如此。他曾对太子说:
“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于此可见,武帝对太子的要求,只是让其成为一个秉承其旨的守成之主。然而“太子宽厚”,对诸事“多所平反”,这与“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是截然相反的。儿子在许多重大方面违背了老子的思想和政策,这必然引起武帝不满与大臣非议。
Âú®ËøôÁßçÊÉÖÂܵ‰∏ãÔºåÊ≠¶Â∏ùÊ∑±Áü•ÔºåÂÅá¶ÇÂàòÊçÆÂç≥‰ΩçÔºåËá™Â∑±ÁöÑÊîøÊ≤ªË∑ØÁ∫øÂøÖÂÆöÈö扪•ÂæóÂà∞ª∂Áª≠„ÄǶÇÊûúÂàòÊçÆÁªß‰Ωç‰∏ÄÊó¶Êàê‰∏∫‰∫ãÂÆûÔºåÊ≠¶Â∏ù‰∏ÄÁîü‰∏∫‰πã•ãÊñóÁöщ∫ã‰∏öÂàôÂ∞܉ªòËØ∏‰∏úʵńÄÇËá≥Ê≠§ÔºåÈì≤Èô§Âç´Ê∞èÈõÜÂõ¢Ôºå§™Â≠êÊòì‰∫∫ÁöÑÈáç˶ÅÊÄßÔºåÂ∑≤ËøúËøúË∂ÖÂá∫‰∫܉∏ÄËà¨Â§´Â¶ª‰πãË∞ä„ÄÅÁà∂Â≠ê‰πãÊÉÖ„ÄÇÂÆÉÂ∑≤ÊíïÂ骉∫ÜÊ∏©ÊÉÖËÑâËÑâ„ÄÅÈ™®ËÇâ‰πãÊÉÖÁöÑÈù¢Á∫±ÔºåÂáåÈ©æ‰∫éÂÆóÊ≥ïÂà∂Â∫¶‰πã‰∏äÁöÑÔºåÂè™Êò؉ΩÝÊ≠ªÊàëÊ¥ªÁöÑ˰ĉ∏éÁÅ´ÁöÑÊñó‰∫â‰∫Ü„ÄÇÂõÝÊ≠§ÔºåËøô‰∏牪ÖÊòØÊ≠¶Â∏ùËìÑË∞ãÂ∑≤‰πÖÁöÑÂøÉÊÑøÔºåËÄå‰∏îÊòØÂøÖÈ°ª‰ªòËØ∏Ë°åÂä®ÔºåÂπ∂Âú®Ëá™Â∑±ÂΩí§©‰πãÂâçÂøÖÈ°ªÂÆåÊàêÁöѧ¥Á≠â§߉∫ã„Älj∫éÊòØÔºåËÄÅË∞ãÊ∑±ÁÆóÁöÑÊ≠¶Â∏ùÂ∑߶ôÂú∞ËÆæËÆ°‰∫Ü‚ÄúÂ∑´Ëõä‰πãÁ•∏‚ÄùÔºå‰∏ÄÁÆ≠ÂèåÈõïÔºåÁ®≥ÂΩìËÄåÊÆãÈÖ∑Âú∞ÂÆûÁé∞‰∫ÜËá™Â∑±ÁöÑÁõÆÁöÑ„ÄÇ
‰ªéÂ∑´Ëõä‰πãÁ•∏‰∏≠Ôºå‰∏çÈöæÁúãÂá∫ÔºåÂú®Èǣ˰ÄÊ∑ãÊ∑ãÁöÑÈ™®ËÇâÁõ∏ÊÆãÁöÑË°®Ë±°‰πã‰∏ãÔºåÊé©ÁõñÁùÄÁöÑÔºåÊ≠£ÊòØÁöáÂƧÂÜÖÈÉ®‰πÉËá≥Ê雷∏™Êúùª∑ÂÜÖ§ñÈÅ•Áõ∏ÂëºÂ∫îÁöÑÂêщ∏™ÊîøÊ≤ªÈõÜÂõ¢‰πãÈó¥ÁöÑÊñó‰∫â„ÄÇËøôÁßçÊñó‰∫âÔºå‰∏é‰∏§ÂçÉÂπ¥Áöщ∏≠ÂõΩÂ∞Ū∫Á§æ‰ºöÁõ∏ÂßãÁªà„ÄÇÂ∑´Ëõä‰πãÁ•∏ÊòØË•øʱâÊó∂ÊúüÁöÑÈáç§߉∫㉪∂ÔºåÂغË᥉∫ÜʱâÊúùÁªüÊ≤ª‰∏ä±lj∫ßÁîü‰∏•ÈáçÁöÑÊîøÊ≤ªÂç±Êú∫ÔºåÈÖøÊàêʱâÊ≠¶Â∏ùÂêéÊúüÊîø±ÄÁ©∫Ââç‰πãÂ∑®ÂèòÔºåÂØπÊ≠£Â§Ñ‰∫éȺéÁõõÊó∂ÊúüÁöÑË•øʱâÁéãÊúùÈÄÝÊàêÂ∑®Â§ßÁöÑÂΩ±ÂìçԺ剪éËÄå‰ΩøË•øʱâÁéãÊúùÁî±ÁõõËΩ¨Ë°∞Ôºå§߉º§ÂÖÉÊ∞î„ÄÇ
2022-08-09 · 答题姿势总跟别人不同

2022-08-09 · 非职业答题人

2022-08-09 · 非职业答题人